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9年7月20日) |
|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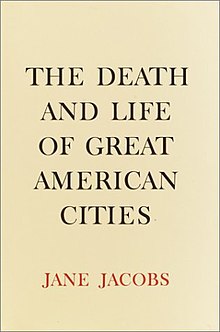 | |
| 中文名 | |
| 作者 | 珍·雅各 |
| 譯者 | 金衡山(簡體中文) 吳鄭重(繁體中文) |
| 語言 | 英語 |
| 主題 | 城市規劃 |
| 發行資訊 | |
| 出版機構 | |
| 出版時間 | 1961 |
| 出版地點 | 美國 |
| 頁數 | 458 (英文1989版) |
| 系列作品 | |
| 續作 | 城市經濟(The Economy of Cities) |
| 規範控制 | |
| ISBN | 0-679-74195-X |
| OCLC | 500754 |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英語: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作家兼活動家珍·雅各1961年出版的一本書。該書對20世紀50年代的城市規劃政策進行了批評,認為這種政策應為美國大量城市的鄰里社區的衰落負責[1]。該書反對當時的現代主義教條,並對美國有機的城市活力提出了獨到的讚賞。
內容
[編輯]雅各布批評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理性主義」規劃者(特別是羅伯·摩斯),認為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忽視並過分簡化了生活在不同社區的人的複雜性。她主張街道要可步行。令她震驚的是,城市規劃者將波士頓北端(North End)充滿活力的地區歸為了需要城市開發的貧民窟。
她特別批評拆除整個街區的市區更新,例如三藩市菲爾莫爾區的案例(Fillmore district),造成貧困居民流離失所。她聲稱這些政策創建了孤立、不自然的城市空間,破壞了社區和創新經濟。(見非場所和超現實)
- 主要用途混合(Mixed primary uses),在一天中不同時段內激活街道
- 小街段(Short blocks),允許更多步行者進入
- 各種年代和修復狀態的建築物
- 密度
有認為她的審美可以與現代主義者的審美觀點相反,鼓勵冗餘和活力而非秩序和效率。她經常引用紐約市的格林尼治村作為充滿活力的城市社區的一個例子。得益於她的寫作和行動,該村莊以及很多相似的社區得到了保留或至少是部分保留。本書還在減緩加拿大多倫多猖獗的推倒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雅各曾在那裏參與阻止士巴丹拿高速公路建設的活動[2]。
簡介
[編輯]雅各在作品開頭說:「此書是對當下城市規劃和重建理論的抨擊。」她描述了1959年去波士頓北端社區的旅途,發現它既友好,又安全、健康,並將她的經歷與她與該地區精英規劃師和金融家的談話形成鮮明對比,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需要更新的「可怕的貧民窟」。她譴責主流城市理論是一種已經滲透規劃者「貌似學問的迷信」,並也同樣滲透了官僚和銀行家的思想,她簡要地追溯了這種「正統城市規劃理論」的起源。
對正統城市規劃的描述
[編輯]在總結當代城市規劃理論的發展時,她從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或譯「花園城市」)說起。有認為田園城市是一個新的總體規劃形式、遠離19世紀晚期倫敦的喧鬧和骯髒的自給自足的城鎮,被農業綠化帶環繞,學校和住房圍繞着一個高度規劃的商業中心。每個田園城市最多可以居住30,000名居民,並追求永久性的公共權力機構仔細規範土地使用,並抵制增加商業活動或人口密度的誘惑。只要掩蓋在綠地後面,工業工廠是允許建在周圍的。田園城市概念最早在英國萊奇沃思和韋林花園市,以及美國新澤西州拉德布恩(Radburn)郊區的發展中得到實現。
雅各通過美國名人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克萊倫斯·斯坦恩(Clarence Stein)、亨利·賴特(Henry Wright)和嘉芙蓮·鮑爾(Catherine Bauer),來追蹤霍華德的影響力,他們是被鮑爾稱為「非中心主義者」(Decentrists)的一群思想家。非中心主義者建議使用區域規劃作為改善擁擠的城市的困境的手段,吸引居民在低密度邊緣和郊區的開始新生活,從而減少城市核心的擁擠。雅各強調了田園城市倡導者和非中心主義者的反城市偏見,特別是他們一些共通的直覺:社區應該是自足的單位;混合土地使用造成了混亂、不可預測和消極的環境;街道對人類互動而言是糟糕的場所;房子應該從面向街道轉為面向蔭庇的綠地;由幹道提供的超級街段優於交叉路口一個接一個的小街段;任何重要細節都應由永久性規劃決定,而不是由有機活力所塑造;並且應該阻止人口密度增加,或至少偽裝之以產生隱秘感。
雅各針對勒·科比意繼續調查正統城市規劃,其光輝城市的概念設想大公園內有二十四座高聳的摩天大樓。表面上看,這與非中心主義的低層低密度理想不一致,但勒·科比意提出的垂直城市,每英畝住1,200名居民,實為花園城市基本概念——超級街段(super-block)——的一種延伸,規範的社區規劃,方便汽車進入,並插入大片草地,以便讓行人遠離街道——進入城市本身,其目標顯然是重新製造蕭條的市中心。在導言的結尾,雅各提到了了城市美化運動,該運動以市民中心、巴洛克式林蔭大道和新的標誌性建築美化了市中心地區。這些努力借鑑了其他背景下的概念,例如與自然步行路線脫節的單一用途公共空間以及對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展覽場地的模仿。
正統城市規劃理念的來源
[編輯]- 埃比尼澤·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 劉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 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進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
- 嘉芙蓮·鮑爾,《現代住房》(Modern Housing)
- 克來倫茲·斯坦恩,《邁向新城鎮的美國》(Toward New Towns for America)
- 雷蒙德·昂溫爵士,《擁擠無益》(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
- 勒·科比意,《明日之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
對正統城市規劃理念的批判
[編輯]雅各承認,田園城市和非中心主義者的想法在他們自己的話語下是說得通的:吸引私隱導向、愛好汽車的人士的郊區小鎮應該吹捧它的綠地和低密度住房。雅各的反正統挫折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的反城市偏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關於如何設計城市本身的主流學術和政治共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課程以及聯邦和州立法中被奉若神明,其影響包括但不限於住房、抵押融資、市區更新和分區決策。「這是這個悲哀的故事中最令人吃驚的事:最終,那些真誠地想要強化大城市的人們卻接受了這些目的非常明確的、以破壞甚至摧毀城市的系統為己任的處方。」她對勒·科比意不太同情,並沮喪地指出對於這座夢幻城市,無論有多不切實際、脫離現有城市的實際情況,卻「受到了建築師們狂熱的歡呼並且逐漸在從低收入住宅到辦公樓等眾多建築項目中得到體現,」 她進一步表示擔心,孤立的城市美化的努力尋求避免被「日常城市」(the workaday city)污染,卻未能吸引遊客而慘澹收場,表現出現了令人討厭的流浪和凋敝破落等傾向,並且諷刺的是反而加速了城市消亡的步伐。
雅各將行人路作為維持城市秩序的中心機制:「這種秩序充滿着運動和變化,儘管這是生活,不是藝術,我們或許可以發揮想像力,稱之為城市的藝術形態,將它比擬為舞蹈。」對於雅各而言,行人路是「複雜的芭蕾舞」的日常舞台,其中「每個舞蹈演員在整體中都表現出自己的獨特風格,但又互相映襯,組成一個秩序井然,相互和諧的整體。」
雅各認為城市與小鎮、郊區根本不同,主要是因為他們充滿了陌生人。更準確地說,陌生人與熟人的比例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平衡的,甚至在他們的家門口,「僅僅從一小塊區域人口的數量來看,這種可能性也是肯定存在的。」因此,城市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讓居民感到安全,並在大量流動的陌生人中融入社會。鑑於其在預防犯罪和促進與他人交流方面的作用,健康的行人路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關鍵機制。
雅各強調,城市行人路應該與行人路周圍的物理環境相結合。正如她所說:「城市的行人路,孤立來看,並不重要,其意義很抽象。只有在與建築物以及它旁邊的其他東西,或者附近的其他行人路聯繫起來時,它的意義才能表現出來。」
安全
[編輯]雅各認為,城市行人路和行人路的使用者能積極參與阻止混亂和保護文明。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安全受益者或無助的危險受害者」。健康的城市行人路並不依賴於持續的警察監視來保證其安全,而是依靠「互相關聯的,非正式的網絡來維持的,這是一個有着自覺的抑止手段和標準的網絡,由人們自行產生,也由其強制執行。」雅各發現,使用良好的街道往往相對安全、免於罪案,而廢棄的街道往往不安全,她認為大量的人的使用可以阻止大多數暴力犯罪,或至少確保一定數量的第一時間反應的人,以減輕混亂事件的影響。街道越是熙熙攘攘,路過的陌生人沿其步行或從中觀看就越有趣,形成更多的無意識的保安,他們可以在麻煩到來前發現跡象。換而言之,健康的行人路將城市的大量陌生人從負債轉變為資產。當街道由他們的「天然居住者」(natural proprietors)監視時,自我執行機制尤其強大,他們喜歡觀看街頭活動,自然地投身於其不成文的行為準則中,並確信其他人在必要時會支持他們的行為。它們構成了管理行人路秩序的第一道防線,當情況需要時由警察當局起補充作用。她進一步總結了城市街道維護安全所需的三個必要素質:1)公共和私人空間之間的明確劃分;2)街道上的眼睛和足夠的面向街道的建築物;3)街道要總有人盯着,保證有效監控。隨着時間的推移,相當多的犯罪學研究在預防犯罪方面使用了「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的概念[3]。
雅各將天然居住者與「過路鳥」(birds of passage)作對比,這些短暫而未投資的街區居民「沒有一點誰在看管着街道或如何看管的概念」。雅各警告說,雖然街區可以吸收大量的這些人,但「如果整個街區的人都變得和他們一樣,他們就會慢慢地發覺街道不安全了,繼而……轉移到其他安全一點的街區,儘管天曉得那裏是不是更安全。」
雅各在空曠的街道和高層公共住宅中空無一人的走廊、電梯和樓梯間之間作了類比。這些「無人監視」(blind-eyed)的空間,仿照上層社會公寓生活的標準,但缺乏門禁、看門人、電梯工、樓宇管理,或相關的監督功能,沒有能力應對陌生人,因此陌生人的存在「自然是一種威脅」。它們對外敞開,但卻無法從外面看見,因此「缺乏一般街道常有的監視和約束」,破壞性和惡意行為頻發。隨着居民逐漸感到公寓外不安全,他們越來越多地脫離建築物的生活,並表現出「過路鳥」的傾向。這些麻煩並非不可逆轉。雅各聲稱,布魯克林項目通過將走廊向公眾視線敞開,成功地減少了故意破壞和盜竊,將它們配置為遊戲空間和狹窄的門廊,甚至讓租戶將它們用作聚餐地點。
基於繁忙的行人環境是城市安全的先決條件這一理念,在沒有狹義的監視力量的情況下,雅各建議「沿着行人路的邊上三三兩兩地佈置」足夠的商店、酒吧、餐館和其他公共場所。她認為,如果城市規劃者堅持忽視行人路生活,隨着街道變得荒涼和不安全,居民將採取三種應對機制:1)離開街區,將危險留給那些無法搬遷的窮人,2)撤退到汽車,只作為駕駛者與城市互動,而永不步行,或3)培養一種街區「地盤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Turf),將高檔社區和令人討厭的環境用防旋風圍欄和巡邏員隔離。
交往
[編輯]行人路生活令一系列日常的公共互動成為可能,從詢問方向和向雜貨店詢問建議,到向路人點頭招呼和欣賞新狗。「大多數事情都完全是小事一樁,但是小事情集在一起就不再是小事。」其集在一起就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張網絡」,其實質上「並不意味着個人必須要承擔的責任」,並保護了珍貴的私隱。換句話說,城市居民知道他們可以參與行人路生活,而不必擔心「糾纏不清的關係」或過度分享生活細節。雅各將其與包括低密度郊區在內的沒有行人路生活的地區進行對比,在其中居民必須將其私人生活的更重要部分暴露給少數親密接觸者,否則就會完全失去聯繫。為了維持前者,居民必須極其慎重地選擇鄰居及其社團協會。雅各認為,這種安排「對那些自我標榜的上中階層確實很合適」,但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完全不奏效。
沒有行人路生活的地方的居民習慣於避免與陌生人進行基本的互動,特別是和那些收入、種族或教育背景不同的人,以致於他們無法想像可以與他人有多深厚的個人關係。在任何繁華的行人路上,這都是錯誤的選擇,每個人都享有同樣的尊嚴、通行權和互動的動力,而不必擔心損害個人私隱或產生新的個人義務。這樣一來,除了公共熟人數量大幅減少之外,郊區居民的社交生活私隱性反而低於城市居民。
孩子的同化
[編輯]行人路是孩子們在父母和街道其他天然居住者普遍的監督下玩耍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在行人路上孩子能學到「成功的城市生活最基本的東西:人們相互間即使沒有任何關係也必須有哪怕是一點點對彼此的公共責任感。」在無數微小的互動中,孩子們吸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行人路上的天然居住者為他們的他們的安全和幸福付出了投入,哪怕他們沒有親屬關係、親密友誼或正式責任。這一課不能通過僱傭幫手制度化或複製,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有機和非正式的責任。
雅各指出,行人路理想的寬度為30到35英尺,能夠滿足一般遊戲的需求、為活動遮陽的樹木、行人行走、成人公共活動,甚至閒庭漫步。然而,她承認,這個寬度在汽車時代是一種奢侈品,但令人欣慰的是20英尺的行人路——除繩索跳躍外仍能夠支持有活力的混合使用——仍然可以找到。即使沒有適當的寬度,只要位置方便且街道有趣,行人路也可以成為兒童聚集和發展的有利場所。
公園的作用
[編輯]正統的城市規劃視公園為「給予城市貧困人口的恩惠」。雅各顛倒這種關係,並「把城市的公園視為是一些『貧困的地方』,需要生氣與欣賞的恩惠」。公園活躍和成功的原因與行人路相同:「周圍地區功能的多樣化,以及由此促成的使用者及其日程的多樣化。」雅各提供四種良好的公園設計原則:互構性(刺激多種用途和反覆使用者)、中心作用(主要十字路口、暫停點或高潮)、陽光作用和封圍作用(建築物的存在和多樣的周邊環境)。
街區行人路的基本規則也適用於街區公園:「生機和多樣性產生更多的生機,而沉寂和單調則讓生機遠離。」雅各承認,在一個熱鬧的社區中心設計精心設計的公園可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由於大量有價值的城市投資沒有資金支持,雅各警告說「休憩玩樂場地和住宅攤用地太大,數量太多,而質量又太敷衍了事,位置又太不合適,因此對使用者來說也就太單調,太不方便。」
城市街區
[編輯]雅各對城市社區的正統概念感到憤怒,在傳統定義下,城市社區是擁有約7000個居民的模塊化、封閉的群體,該人口大約為支持一所小學、便民商店和社區中心的規模。雅各認為這個定義是狹隘而隨意的;偉大的城市的一個特點是居民的流動性和不同大小、特徵的不同區域的使用流動性,而不是模塊化的碎片。雅各給出的替代方案是在三個層面的地理和政治組織下定義社區:城市層面、街道層面和地區層面。
整個紐約市本身就是一個街區,也是公共資金流動、行政和政策決策,以及代表地區解決一般福利衝突的「父母」街區。創建志同道合的社區、協調當地的活動的公民協會和特殊利益集團——從歌劇社團到公共工會——通常在城市層面形成。在尺度的另一端,單獨的街道——例如格林威治村的哈德遜街——也可視為街區。如本書其他部分所述,街道層面的城市街區應該追求足夠頻繁的商業、普遍的活力、使用和關注,以維持公共街道生活。它們不是固定長度的離散單位,而是所有鄰近街道街區的經濟和社會連續體。
最後,格林尼治村地區本身就是街區,具有共同的功能身份和共同的特性。地區的主要目的是協調街道街區的需求與城市層面的資源分配和政策決策。雅各估計,一個城市地區的最大有效面積為20萬人和1.5平方英里,但相對空間上的定義,她更推崇功能上的定義:「大到足夠能與市政廳進行抗爭,但是不能太大,以致街道街區無法引起地區的注意,也就說不上話了。」區域邊界是流動的和重疊的,但有時由物理障礙物如主要道路和地標界定。
雅各推薦的城市有效街區規劃的四大支柱是:
- 造就生動有趣的街道
- 在城市轄下具有小城市的面積和力量的地區內儘可能地促成具有這種特性的街道網
- 將公園、廣場和公共建築作為街道特性的一部分來使用,從而強化街道用途的多樣化,並將這些用途緊密地編織在一起。公園、廣場等的使用不應該各行其事,互相分離,或與地區內的街區的用途互不關聯
- 要突出一些地域的功能身份
雅各布最終將街區質量定義為一種隨着時間的推移,採用住宅合作、政治影響力和金融活力的組合以治理和保護自身的功能。「一個成功的街區應該能夠知曉自己的問題,不至於導致問題成堆而積重難返。失敗的街區是一個被問題糾纏,甚至在越積越多的問題面前無可奈何、不知所措的地方。」
遺產
[編輯]本書仍然是雅各最具影響力的書,並且仍獲規劃專業人士和公眾廣泛閱讀。它已翻譯成六種語言,售出超過25萬份[4]。城市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雖然對她的方法論有所批判,卻鼓勵了雅各在「紐約書評」中的早期寫作[5]。 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引用雅各的著作並視之為對他為羅伯·摩斯立的傳記《權力經紀人》(The Power Broker)一書的最大影響。Samuel R. Delany的《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一書很大程度上依賴《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來分析城市研究領域內社會關係的本質。
參考書目
[編輯]-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odern Library (hardcov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February 1993 [1961]. ISBN 0-679-60047-7. This edition includes a new foreword written by the author.
-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on Jane Jacobs' Legacy. Toward a Jacobsian theory of the cit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Robert Kanigel. Eyes on the Street: The Life of Jane Jacob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6. ISBN 9780307961907.
參見
[編輯]- 通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CPTED)
- 防禦空間
參考文獻
[編輯]- ^ Jane Jacobs' Radical Legacy. Peter Dreier. Summer 2006 [2012-08-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9-28).
- ^ Cervero, Robert (1998). The Transit Metropolis: A Global Inquiry, p. 87. Island Press. ISBN 1-55963-591-6.
- ^ Paul, Cozens,; D., Hillier,. Revisiting Jane Jacobs's 'Eyes on the Stree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vidence from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The Urban Wisdom of Jane Jacobs. 2012 (英語).
- ^ Ward, Stephen: Jane Jacobs: Critic of the modernist approach to urban planning who believed that cities were places for peopl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n The Independent, 3 June 2006
- ^ Jane Jacobs Interviewed by Jim Kunstler for Metropolis Magazine, March 2001. [2006-04-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4-26).

